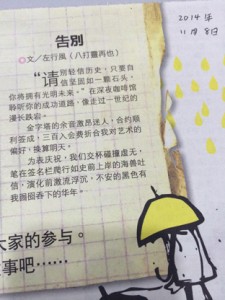生活無處不詩。吃蘋果有詩。唱一首情歌有詩。看一場文藝電影更是一首詩。如果真是這樣,我想要請問的是:「迷路是不是一首詩?」
話剛說完,我姐舉手就要揮下,「你這是怪我帶錯路嗎?」
我聳聳肩:「說來逛商場的是妳。說徒步走一段路去比較方便回家的捷運線路也是妳。妳說,我還能說什麼?」
「閉嘴。」我姐說,算是長輩的她不須理會我的抱怨,「平時搭捷運都會經過這個路段,我記得是往這方向去的,怎麼又會不對了?奇怪。」
無論有沒有人願意聽,我有話要說。我認真覺得,我姐其實一點兒都不須要那麼懊惱。就好像那天我約了一個貨去雙威金字塔約會那樣,我問她妳會去嗎?她說我會我會。會到最後我們還是在富都車站旁的茨廠街吃外勞弄的燒魚。味道和本地馬來仔弄的也差不多。就好像天下的燒魚都差不多一樣味道,總有很多的人喜歡不懂裝懂,苦了別人也苦了自己。
「啊呀,我的鞋子穿反了,難怪我找不著方向。亞弟,來幫我把鞋子穿正。」我姐說著就走到一面牆邊倚著,示意我快點手。不會有時間考慮「鞋子穿反」和「迷路」是不是有它們的邏輯關聯。我迎上前去,蹲下半跪在我姐跟前,給她玩鞋。「姐,妳靠在兩棵椰樹之間呢!」當我仰視著我姐,才在不經意間瞧見已被我姐的影子半遮的椰影。「看!是一幅壁畫,還蠻漂亮的。」
「是嗎?」我還沒來得及替我姐反正她的鞋子,她便已蹦起看賞那幅壁畫。我們才發現原來在兩棵椰樹之間,還畫有個面目模糊不辨男女,雙手各握酒瓶躺在一塊紅布掛就的吊床上的人,搖頭晃腦地,該是喝醉了吧?
「多美的詩意。」我姐說著,臉則貼到離牆非常近的位置,「你瞧這牆痕斑駁,道道都是歷史的刻痕。歷史縱使被大多數人遺忘,卻不會被我這類人放棄。我想,這牆前牆後的,定有許多被日日路過的人所無視的故事,你說對吧?」我姐就像著魔了一樣,循著這面牆緩緩地移動,像在尋找著什麼。
我必須承認,我實在進不了我姐這些文人的心理世界。歷不歷史其實與我無關,更別說牆上的斑駁了。我在意的是今晚去另一個貨子家看恐怖電影的約會。如果事情一直被我姐這麼亂搞下去,我鐵定會遲到甚至去不到,明天那大小姐就會隨便在學校找個男生聊天,給我戴綠帽。
不行!男子漢大丈夫,為了避免綠帽危機,我決定——啊!祗感覺到手腕一陣痛,我身不由己地被我姐拉著走。我姐拉著我沿那牆一路快走,牆不長,我們在一扇老舊的鐵門前停下。
「看,這是通往歷史的大門。」我姐興奮十足地說著,「有點英化風格的古堡式大門。鐵門對上刻的『1895』該是建成年份。至今……嗯,該有百多年歷史了吧。亞弟,現在你或許無法理解,但當你發現時,歷史的沉重與疼痛就會在那裡。」我姐說完便要動手去推開那扇鐵門。我不知道她怎麼發現這扇鐵門,但是:「大姐啊,妳沒看到門旁『關閉,禁止進入』的告示牌嗎?」
我並不想過多關注因猛然中斷肢體動作而看起來有些僵滯的我姐。我想她連這是幢什麼樣的建築物也不清楚。終於鼓起勇氣,「或許我們都該回去了?」我說,「時間不早了。我肚子餓了。」理由比較一般,但在外頭走走站站這麼久,的確很容易肚子餓。
我姐像是聽見了我的抱怨。怪的是她沒罵我,祗不停呢喃什麼飢餓什麼空虛。過了好一陣子,我才忍不住試探性問了聲:「姐?」
「啊?」她驚醒似的,臉色迷糊問我:「我們該怎麼回去好?」由於四周再沒有其他人,我祗當她是在問我,雖然她依然雙眼直愣愣看向那扇鐵門。「不如……我們問人吧?」我放低聲量,希望她能接受我的建議,這樣我或許趕得及赴約。我姐點點頭,沒跟我打聲招呼就慢步走開。
然而在好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沒跟任何人交談,我祗靜靜跟著我姐走。然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麼從而說出那安靜走過好長一段時間裡屬於我們的第一句話:「姐啊,妳的鞋子還沒反正過來耶。」
× 本文入圍2012年馬來西亞華文微型小說創作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