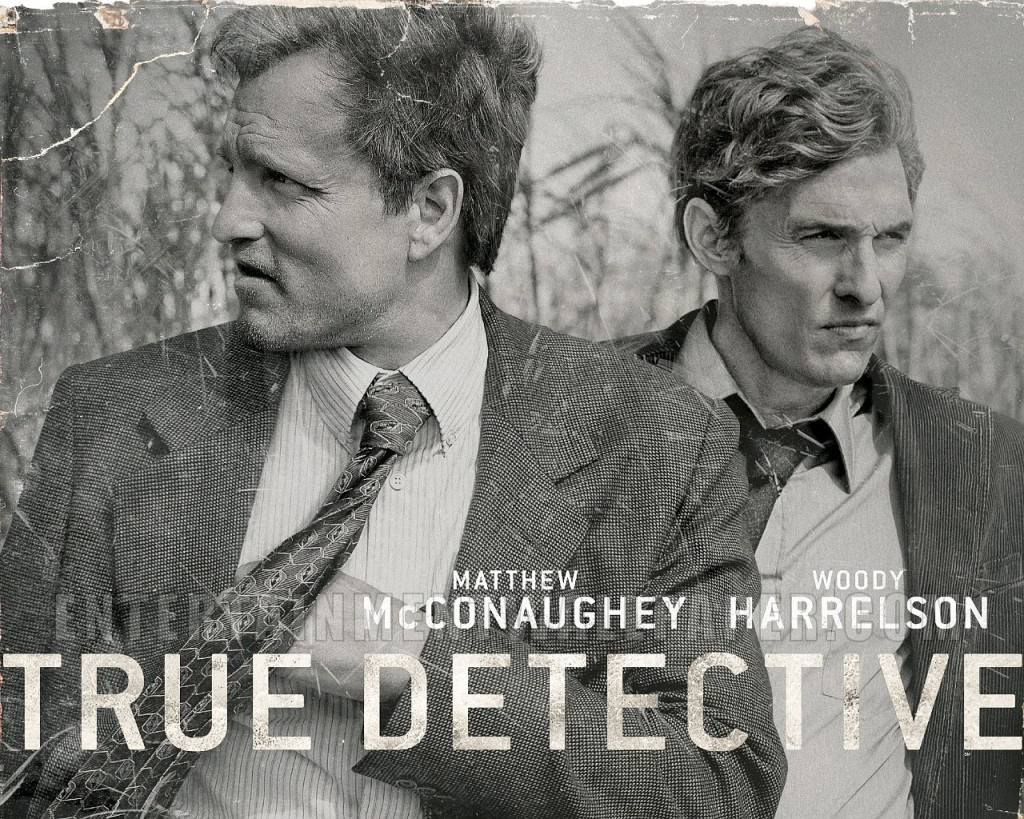就像有隻蒼蠅飛過來,對不起不是一隻,是一堆蒼蠅在你耳朵邊吚吚哦哦,直飛入你的腦袋裡頭——救命呀救命呀——啊,想起嗚嗚祖拉!這個從南非世界杯開始廣為人知的大喇叭,已經從電視進駐到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電視機有導播和調音師降低噪音,現實中你只有啞忍了——難怪有人說,那是對運動的另一種“消音”。而冼文光這部饒富政治意味的長篇小說,取《蒼蠅》之名,也頗有噪音之感。
這部小說架構了一個類似馬來鄉村的空間。雖然可以看出有許多明顯的現實政治符碼,但它們都只是錯身而過的蕪雜資訊,對主角群——高潮、豽吉布、呂含娜、夏娃、阿妲托婭等等——而言不具有意義。他們認知的世界被性與鬼怪填滿。男子想著找女生打炮,人跟鬼可以做愛,諸如此類。
任你城區如何如何,這群活於國內之國的人們自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持平而言,這暗合了本地部份政治現實——城鄉的對立。不過你要真對之分析個所以然來,很抱歉,大多數人都只能人雲亦雲地說上幾句刻板分析。換句話說,我們對“那裡”的認知必然帶有某種缺乏現實基礎的想像——同時,也是《蒼蠅》的立足點。
冼文光不僅割裂鄉村與鄉村之外的空間連接,還將村內的生活切成零碎的圖像,跳躍性地說著不怎麼精彩的故事。主角群和那本斷章缺頁的“記事簿”交叉出現,卻不提供足夠的線索讓讀者將各種碎片重新拼貼起來。還是作者完全不在意意義的重新拼貼呢?《蒼蠅》的書寫形式足夠前衛,論內容卻流於空中樓閣式的空想,平平無奇。
更甚者,各個人物雖不共享同一個名字,惜敘事技巧平面,全書下來持的都是同一個腔調,每個人物又像同一個人物,沒有個性,面目模糊。不清楚作者是刻意如此,或走不進那樣的世界塑造那樣的人物?但這些對閱讀的干擾是嚴重的,正如書名所開示的,只聞噪音響,不見人(故事)出來。
為了讓世界更清淨些,迫於無奈只好手起刀落:你寫壞了。
書名:《蒼蠅》
作者:冼文光
出版:有人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星洲日報/本報特約:左行風‧2015.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