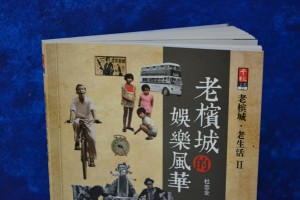自90年代當政者解禁馬共,相關在野的書寫與研究逐漸開展。當馬來亞半島還是殖民時期時,華人基於淘金或躲避戰禍理由來到南洋,心態上屬「僑民」意識,這點在各造研究中幾無疑慮。麥留芳則從一相對特別的視角觀察早期馬來亞華人的國家與社會認同:愛國歌曲。
此書為單篇論文出版成書,劃1930至1970年代為限,觀察馬來亞華人社會在愛國歌曲方面的反應。由於紮根此地的觀想在當時仍未形成,所謂愛國歌曲,往往多與中國時局有關,開始時由南來合唱團引進,後來因著抗日與反殖民才漸漸有了與在地相關的題材出現。據麥留芳,可分成六大類:
一、共產國際歌;二、中共革命、頌揚軍國領袖歌曲;三、國民黨的抗日、軍歌等;四、馬華武裝部隊支援英殖民政府及中國抗日的歌曲;五、馬共反英殖民的歌曲;六、民謠、勵志和反封建的電影插曲。
其時的僑民仍以中國為祖國,唱中國愛國歌曲自是無可厚非。關鍵問題在於,從這左、右翼共存的六大類中,無論華僑如何選擇自身的意識形態,礙於時局,他們對「祖國」的政治認識必定有限,尤以華僑第二代為甚。
如此,「中國」則淪為想像中的意識認同,與個人切身之處境分割開來,也就是此書所說的「虛擬認同」了。麥留芳這一段寫得好:
「當這些歌曲由中國的歌劇團帶到海外時,為華僑提供了『國家認同』的動力。不幸的是,這個認同卻因中國國內的豆萁煮豆的行為,其之劇烈、快速、多端必然使到華僑無所適從。這種認同的失落,便在他們後來不擇歌曲而唱的行為上表露無遺;這便是虛擬認同的一種。除了恆常臍帶文化外,個人的經驗與歌曲中所言之事物及人物,並沒有實質上的關聯。」
書中錄有多首當年在馬來亞流傳的華人愛國歌曲。我們祖上曾高唱過「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大海航行靠舵手》,還有「我們是陳平同志的好戰士/在烈火中鍛煉,在暴風雨中成長……豪情激盪,無上榮光」《我們是陳平同志的好戰士》。
如今,至少從政治體制上來說,馬來西亞大體屬於民主政治,華人的家國認同已完成從中國而在地的過渡。回望過去,想像我們祖上那段或也曾熱血過的革命歲月,分處兩個歷史情境的我們互相凝視的目光,竟如此陌生。這類歌曲,我們這一代人無疑已唱不出口。祗得啖笑。
‧書名:《虛擬認同:早期馬來亞華人的愛國歌曲》
‧作者:麥留芳
‧出版社:華裔館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左行風‧2014.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