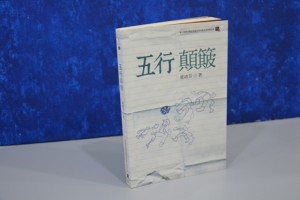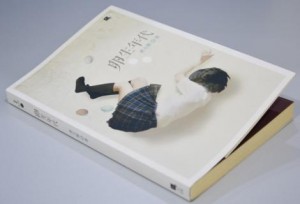二〇〇五年七月八日那天,你以蚊子、雨季和月光寫就一首詩。不禁開始猜想你在什麼情景寫下這首詩。有蚊,多半不在室內;你的雨裏有如鯉魚蹦跳的路人,應不在鄉郊野外;而月光起舞,「醉是一種放大的理智」——想是在都市酒吧的露天座位看雨賞月飲酒?呵,這樣猜詩畢竟還是太執著於形呀,境界自低,月和雨有同時看見的可能嗎?
這一輯題為〈近乎遺忘〉的詩,反以日記為題,按時間從二〇〇八年逐漸倒序至二〇〇三年,意在從現在往回憶的迴廊摸索,說著自我的私語,而當中僅有一篇時間線錯置前後的〈新土——美國入侵伊拉克〉,失序裏有某種節制。
節制有時是種潔癖。徘徊在放與收、言與不語間,字句的一雕一琢均如一潔癖者,忌一切有餘。「指甲的漣漪急速漫延/半圈,半圈——潔癖者為了圓滿/深度切入,乃流出/血絲」〈寫詩〉。指甲深刺肌膚,痛入骨髓逼出了生之感悟,是為詩,是為血。
血可以是一個系,譜系的系。「血使我們像河水/在一個看似封閉的系統中/流下去。」〈血〉鹽把血濃化,而終有肉體無法承載的那一刻,自而低落紙上。如果血是愛情的,那會是首情詩:「不要說沒有關係,我寧可你看/不見,我寧可/你不要看見:我是你的血。」〈系〉副作用:傷口會變痛。
痛楚是比鬧鐘更有效的提醒劑。痛讓你感到盼望,感到存在,回顧了地獄那頭前足搭在肩上的狼。鯨向海說,並不確鑿讀到和一般台灣詩人的明顯差別。但若多用蕉風椰雨,反失之刻意兼矯情吧?「腳下的生活/是本土就不必化/再化也非本」〈體物〉。
詩集以《鹽》為題。鹽是最古老的調味物,也是詩人在生活上嘗到的奧秘之味,獨沽一點但未必一味,詩作始終還是結晶品。至於它引發了什麼味道,則任由老饕細品。惟食鹽過多,恐對人體造成損害,請節制服用。
書名:《鹽》
‧作者:邢詒旺
‧出版:有人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左行風‧2014.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