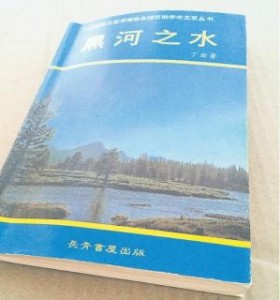前段時間隨巫統大會而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紛爭,紛擾了好一陣,最後也隨著大會的結束與過去而塵歸塵。一如往常,正反雙方都祗是百無聊賴地自說自話。針對漸趨極端的種族及宗教主義言論,有人想談中庸,但又說不出如何以中庸價值來正面回應對方的內涵。意義層次的落空,導致我們陷入雖(想要)中庸理性而不可得的窘境。提出問題之前,我們還可以問:馬來西亞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一個馬來西亞,兩種社會契約?》是一本由三位學者——奧托曼、普都哲里、凱斯勒——合著的小書。他們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多年,並且在這部書中,用「社會契約」的政治概念貫穿梳理了從建國初期至今,馬來西亞是世俗或回教國定位之演變,從而反思今日馬來西亞的社會分歧。
社會契約原本祗是一種解釋人與政府關係的概念,它主張:人類為了個人與集體的福祉,同意讓渡某些自由與權力予一小部分人手中,以獲得政治秩序的好處。另一方面,一旦政治秩序崩壞,公民有權利通過選舉等手段尋求改變。然而,這源自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原本祗是經想像建構的公民與公僕的主從關係,放在馬來西亞新生的歷史框架中,各民族代表黨從英國手中接管馬來西亞的立約日,至今也不過才半個世紀而已。
臨近的歷史日子,客觀上提供了人們對「社會契約」予以具體化的空間。當初立約的時機、動機、條約等客觀條件,均默認為馬來西亞公民必須接受和同意的合約條款,並且在政治場域的論辯中,多次被世俗化及回教化兩大陣營招魂,以獲得自身的正當性。無論雙方立場的正義或否,將精神概念的「契約」視為永恆權威的視角,似乎已為多年來馬來西亞社會走向兩極化埋下伏筆。
凱斯勒認為,國陣政府倒向種族及宗教主義,是鬥爭中落敗於回教黨的政治訊號。他指出:「國陣政府領導人在麗娜喬案判決後,更否認和駁斥馬來西亞是以『世俗國』性質立國的歷史理解和事實。政府接受這樣的結果,標誌五十年漫長鬥爭的結束……新的康莊大道正在召喚,而路牌清楚指示著『回教法』。」
在一些民主比較成熟的國家,通常有兩個大黨,他們的分歧不是各代表某個族群發聲,而是意識形態與資源分配之爭。按三位作者的考究,馬來西亞建國之前也曾有過以意識形態為旗幟的政黨,祗是隨著種族政黨的抬頭而慘敗最終解散。雖然如此,他們仍認為,從諸多建國先賢回憶錄及政策實施推測,馬來西亞最原初的社會契約,應是基於對世俗化及普世價值的認同而建立的,但種族性政黨延伸出的種族政治之爭,則讓此一契約推往另一個方向走,形成「兩種社會契約」。
馬來西亞獨立至今已有58年。我們還得遠繞多少年月,才繞得回58年前那條歷史的岔道?
‧書名:《一個馬來西亞,兩種社會契約?》
‧作者:諾拉妮·奧托曼,瑪維斯·普都哲里,克萊夫·凱斯勒 合著
‧出版: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左行風‧2015.02.01